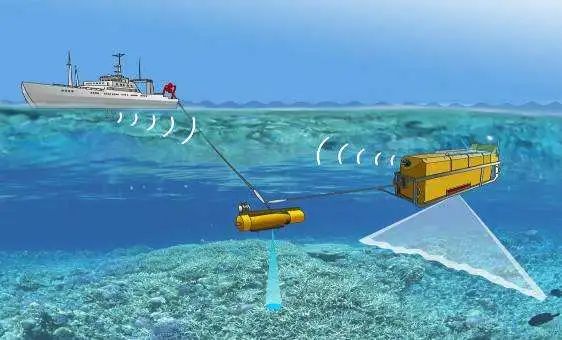- 相关链接
- 中国海洋大学 | 中国海洋大学物理研究实验室 | 迎新网 | 海洋大学堂 |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 | 海大附中 |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 | 西海岸校区建设 | 教育基金会 | 校友会
2019年10月,笔者在天津参加中国海洋档案馆馆藏展仪式,在馆藏文献中第一次看到1963年5月,国内29名海洋科学家联名上书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集体签名名单和29位先生的照片。面对诸位先生的遗照,参观者心潮难平,而更让人敬仰不已的是笔者1971——1974年在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声学专业上学时的导师杨有樊先生竟是29位科学家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一位海洋物理学家。 近60年了,此事先生从未向外人说起,自然他的学生们无从知晓,因为先生生前关于此事未曾向他的学生们透露过只言片语。 笔者已从海业50余载,当面对先生遗照的那一刻,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出更加崇高的敬意,同时心里涌上一阵阵酸楚。凝望杨先生那熟悉的慈祥面容,笔者不由得在心底轻轻地呼唤:老师,学生想您了! 杨有樊,山东济南人(1912—1983年),193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山东海洋学院,曾任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主任、山东大学无线电子学教研室主任、水声研究室主任、山东海洋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声学学会理事、中国海洋物理学会理事长、山东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青岛市物理学会理事长、青岛市政协常委等职…… 杨有樊教授在海洋物理水声学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他从事教育工作四十七年,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为我国海洋水声物理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物理系创建与发展初期,他在王淦昌教授指导下做过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研制出高机械强度的钛酸钡并在定型后批量生产,成为我国较早生产压电材料的单位,满足了国内装配水声换能器的需要,为我国刚刚兴起的水声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培养的大批水声专业人才在学术上都有较高的造诣,他在学术上成为学科带头人,在水声学实际应用中成为业务骨干。 作为我国仅有的几所教授水声物理学的高校,杨先生秉承授业布道理念授课,讲授“声学原理”等多门课程,先后建立了多个“原子物理实验”等多个实验室。山东海洋学院成立以后,他对海洋物理系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物理系设立初期,面对只有六名教师,五名职工的情况下,他亲自领导参与,创建了符合综合性大学物理系的要求和海洋物理学科特点的海洋物理系。在海洋物理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杨有樊教授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努力,为海洋物理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有樊教授工作积极认真,兢兢业业,在他晚年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天,还在为真空实验室的建设外出奔波。他病危躺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物理系的工作和实验室建设。他工作作风勤勤恳恳,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热爱集体,廉洁奉公。既使是在文革中他被错误地定为“国民党特务”,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期间,他仍然矢志不渝,授业布道水声科学,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乐于帮助和指导青年教师,不愧为学子的良师益友,水声专业学科发展的授业布道之师。 杨有樊教授对学子谦逊有嘉,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多年后每当提起杨有樊教授,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学子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尊称他杨先生,无不感慨:杨先生不愧为我们的良师和恩师。 先生,学生想您了! 您是海洋水声学的授业布道之师! 这是笔者发自心底的呼唤,顿感愧对先生的在天之灵。其实,想来也很简单,人生为人学子是一门必修课,正是因为学生也老了,才有了今日的愧疚与深省。 自古有“一字之师”的美谈,然而今天对“一世之师”理解的人有多少?能有多少身在讲台者会心存师者之德?又有多少学生还能真正的去深省对老师的感恩? 师德与师恩是一种文化与文明的伦理。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叶圣陶说:“身教最为美,知行不可分。”而爱因斯坦说:“我确实相信: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的损害。”那么这一教育伦理的道场在哪里? 我国海洋声学教育与科学研究起步较晚,但中国海军的发展却是急需。对此,杨有樊先生时任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系主任期间十分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对开设的教学课程更是高度重视。声学专业的教师严国光回忆:1971年,杨先生力主开设声学专业第一门基础课——振动、波与声,后改称声学基础。 对杨先生高度重视水声学基础理论教学的坚持,笔者想说: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水声专业是海洋声学学子人生的母校;杨有樊先生是母校的授业布道者。 作为一名昔日先生的学生,后来的记者、学者、作家,老来已记不清曾赞美和颂扬了多少德人,可为什么少有赞美自己的母校,颂扬自己的老师?! 愧疚是一剂良药,苦尽甘来让我回味无穷,古稀年后才献上一首迟到的歌: 儿时,母校是一首儿歌,今天唱了,明天还是唱不够。 年少,母校是一首诗,今天读罢,明天想着另一首。 青年了,母校是一篇散文,今天学过,明天还不能理解透。 上了大学,母校变成了一座宫殿,今天求知若渴,明天憧憬着未来的成就。 后来,母校慢慢变成了心中的影子,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离她越远,离别越久,心绪更沉,思念更久。 光阴流逝,我多少次向岁月发问:山东海洋学院,老师您在哪儿…… 现今,爱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字眼。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爱字却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同时也是人们十分慎用的字眼。 爱究竟是什么? 这恐怕是常人一时难以涚清楚的,如歌中所唱:“说也说不清楚,糊里又糊涂……” 但我想说,好感,喜欢可视为一种爱;相识、相知可视为一种爱;相遇、投缘可视为一种爱;交集、碰撞也可视为一种爱;思念、怀念同样是一种爱……。爱的内涵与方式千万种,而最终可以结出真爱果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爱,是付出、责任与沉重的脉生。付出意味着无功利代价,责任意味着责无旁贷,而沉重却是来自思想深处的精神压力。所以,老年人一般是不会轻言爱的。然而,当老了真有了一种爱的感觉时,将会比年轻时更加强烈,这便是言之不出,放之不下,挥之不去的师生之爱。 或许是因为经历多了,自然对发生在身边的许多事情少了年轻时的冲动与激情,其实主要是因为随着老去,多了人生的积累,思想和感情变得厚重,既便悟到了真爱也难以启齿罢了。 厚重是岁月累积的结果。可尽管厚重了,但思想深处仍不失萌动,有另一种异样的冲动,它是一种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情感和岁月阴影的激情,也会在美酒与咖啡,市俗与阳春,鲜花与铜锈相交织时坠入一时的迷惑。 老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记得,那是40多年前的一个漆黑如墨、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晚自习,不经意间一位长者轻轻地坐在身旁。啊,杨先生…… 那时的杨有樊先生是我们的水声专业老师。那年他已年近六十,瘦高的身材,满头银发已难见青丝。当时他还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可他却静静地来到了我的身边。 没待我说什么,杨先生已把手杖靠在课桌边,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上面的雨滴。当他重又戴上眼镜后,顺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手。此时此刻,他用那透过深度镜片的目光示意我不要出声继续学习。 那个晚自习,是令我一生都忘却不了的一次晚自习。自打孩童时起,教授称谓在我幼小的心中就是神秘和神圣的,在这之前我无缘与教授相邻而坐。今天当一位花甲教授对一名学生倾注呵护之情时,学生的心被震撼了。也许是物理的声学知识直接应用于舰艇的缘故,从那以后先生不知多少次关心我,关心一个水兵学生的学习,同我讲海军、舰艇、声呐、水雷……。如今,先生已故去多年,可他那期待的慈爱目光我从来都无法忘却。 今天,我终于可以说:老师,先生,就是那一天我从您身上感受到了身外世界的博大和时光的浩瀚,感悟到了生命的长河中将要接受的一次次无言的承受,无论未来做什么,这种承受都将使我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和担当。 在学生时代结束后的人生旅途中,我时常摩挲起过去的记忆,常常想起那些已经被苍淡的记忆所覆盖的学生时代。在又一次的感受时,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将面对的人生路上还有类似的感受。如今我已走过了人生长长的一大截路,而我却在很长的时间里不知道曾给予了我慈爱的老师杨有樊先生,于1983年1月14日那个风云惨淡的日子永远地离去了。 事后另一位老师告诉我:1983年下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杨先生身体病弱实难坚持上班,但他仍然时刻关心教研室的教学工作。当他听说由北大组织的全国高校物理学教学评估的消息后,他约来任课教师叮嘱:“今后我们一定要重点抓好理论物理课程的教与学的质量。”同时高兴地告诉在场的任课教师:“通报你们一个情况,我校已被教育部批准招收研究生了,物理系被批准第二批招生,声学专业一定要保证质量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1974年夏,笔者毕业告别了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后因工作需要弃理从文而未从师训。退休之后,当笔者见到其它的老师,呈上刚脱稿的一本书稿请老师阅示,并问及“可否敬请转呈杨先生阅示”时,那老师疑惑地问:“这是你迟交的作业吗……?”说完老师笑了。 当年老师的笑声让我褪去了年少时无知的笔墨,保留下了那种不能复制的纯净,抖落了一切本不属于个人的虚无,只有在这时我才深切地感悟到某种时空的人生真情。 直面人生,今天我终于可以不无尴尬地说:“先生,学生想您了。”同时还想说:“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杨有樊先生师德不朽!”